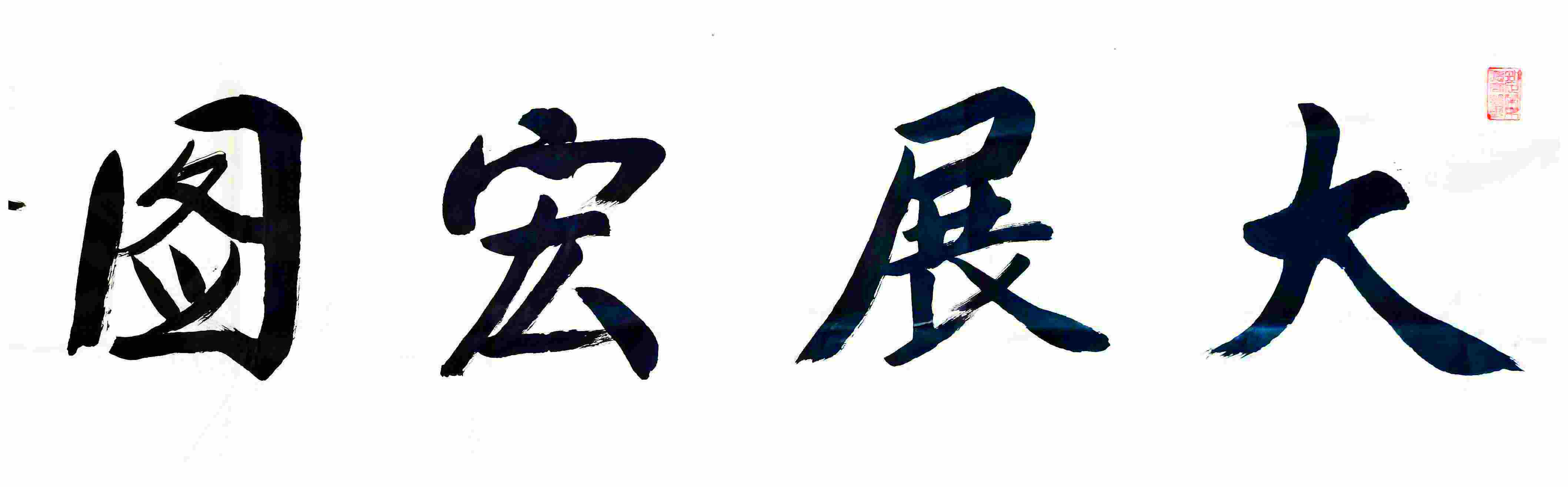道教为什么斗不过佛教?
中国宗教历史上有几个大题目颇让人揪心,来自异域的佛教为何能征服中国?道教为什么比不外佛教?宋代以后佛教为何走向衰落?政府如何控制宗教财产?中国古代的宗教“入世之深”,往往是现代人很难理解的。今天给大家推荐一篇文章,关注一下历史上的佛道之争,本土的道教为什么斗不外外来的佛教?
道教最初是如何传播的?
首先,关于明帝梦西方金人、派人去西去求法的题目,学界已经有大量研究来反驳这样的叙述。佛教进入汉地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应该是西域的商路以及沿着商路展开的职员与观念交流,佛教最初就是由西域的胡人传播的。在曹魏鱼豢所撰的《魏略·西戎传》中载有大月氏王派伊存来汉地授经之事,那个时候就比汉明帝要早;此外,在《后汉书》中就有关于楚王刘英在明帝求法前祭奠浮屠的记载。
根据《后汉书》的记载,刘英喜好神鬼方术,西域来的胡人刚好可以给他提供炫惑之术,浮屠也因此成了他的祭奠对象,季羡林先生用音韵学的方法考证出浮屠即为佛陀。因此,“永明求法”还是商定俗成的历史叙述。
学术研究中,历史现实和历史叙述往往是分离的,历史现实要比历史叙述要复杂得多。学术研究往往将一个历史事实简化之后再叙述出来,让它呈现出独特的线索感与趋势感,考虑历史题目的时候,需要首先对历史叙述的性质有一个清醒的熟悉。
张衡在《西京赋》中“展季桑门”并用,将柳下惠和沙门并提,诠释不近女色之意,说明在张衡那个年代已经知晓沙门不近女色的戒律,这一点在张雪松的《中华佛教史》第一卷中特意指出来了(《中华佛教史》由季羡林、汤一介二先生主编),极具启发性——佛教观念的进入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和多元,并不是依靠某一个历史事件达成的。
道教最开始是如何泛起的?我们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去考虑:第一,道教的基本信奉观念的缘起是什么,是什么时候泛起的;第二,以我们看到的道教基本观念所形成的文本(text)是什么时候泛起的;第三,利用这些观念去进行有组织的宗教和信奉流动是什么时候泛起的。
学界一般将张陵创立的五斗米道(又称天师道)作为最早的道教信奉组织。为什么把五斗米道视为道教的一个发源?基本原因是它的组织性和接近于一个政教合一的特性。述及道教的信奉观念,比方说不死的观念,不死之药的观念,摄生求仙的观念,它们泛起的都非常早,可以追溯到年龄战国乃至更古老的历史传统。道教最早的信奉观念文本是《太平经》(《太平清领书》)里的,其中聚合了大量既有的信奉观念)。
从历史史料和详细信奉形式上看,五斗米道、张角的太平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若我们依照关于张陵的历史记载,张陵是沛人客居蜀地,沛这个区域的确和太平道的流动范围比较接近。陈寅恪先生和柳存仁先生的研究中都已讨论过这个题目。
不妨说,道教并不是在特定的历史时间点上泛起的,道教的缘起及其发展出发点很大程度上决定于道教本身的定义方式。
我更加倾向于以为,道教的信奉发展及观念积累是一个漫长的演进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道教信徒和信奉实践者对于道教信奉的独立性及排他性认同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清楚,更大程度上它是一种自发的信奉实践,而不是有意图的创教冲动。
对于耶稣基督来说,他有一种很强的创教冲动么?或者说他有一种很强烈的创造新的信奉传统的意图么?他不是没有,而是说真正这个传统被建立起来的时候是在耶稣基督之后的使徒和罗马时期。
同样的,王重阳有很强的创教冲动吗?未必,但经由丘处机等全真七子,加上加上尹志平、李志常、张志敬等后代高道的努力,全真道才被建立起来。不妨说,在创教者之后具有信奉热情的第二代、第三代信奉实践者才是信奉传统的真正创立者,也是最富创造力的信奉气力。
换言之,信奉传统的确立和创教是两回事,同样的,创教和信奉观念的缘起也是两回事。
故而,我们今天看到的良多历史记载实在是相冲突的,柳存仁先生有篇很闻名的文章《张天师是不是一个历史人物》就在讨论历史资料中的张天师到底是谁。现在的历史史料和文献记载中,独一能够确证的仅是张鲁传记中的陈述,他的祖父是张陵、父亲是张衡,退一步说,这样的描述是不是张鲁自己说的都无法考订了。当然,从信奉意义上看,《汉张天师世家》中已说的非常清晰,且十分细密。我想把这些题目做一个统合的说明,道教发源需要在历史发展的语境中首先确认何谓道教。
“佛道之争”为什么会产生?
提及佛道争论,先要把两个东西分开:首先是佛道之争与夷夏之争的区别;其次是将佛理和佛教分开。
汤用彤先生说:“佛说其有二端,一者为教,二者为理。”汤先生尝试说明,佛教的“理”与中国的“理”是契合的,比方说魂灵不灭,慈善好施,善恶有报等,这些与中国的传统理念有契合之处;与此相对,“教”是另外一个概念,比方说它具有组织性和排他性。以此为基础,才能考虑佛道争论的题目。
“佛道之争是什么时候开始的”这个题目,学界讨论的已经十分丰硕了。我以为,可否换一个视角,讨论佛教融入中国时采取的策略。作为胡人的本土宗教,佛教是通过西域商人到长安、洛阳等地展示和传授给我们的,或者在胡人的日常交往中,我们受到了他们信奉的影响。
试想,第一批中国人是如何理解佛教信奉的呢?佛教首先被以为是道术的一种。魏晋时期,人们视佛陀为“大圣”,以为其有祛鬼除魔的法力,换句话说,它在我们日常糊口中的概念实在是法力,而不是佛理或复杂的思惟体系。
对于佛道之争的“争”,可以考虑,“争”的含义是什么?要么在争辩一种道理,要么争执一种身份,要么争夺一种资源。从争辩道理的层面上,佛道之争并不存在,对道教来说,所有在本土和糊口世界中泛起的观念,都可以毫无障碍地融入道教之中;在身份和糊口方式认同意义上的差异则很简朴:假如你信奉佛教,那么你对佛教基本糊口要求有一个基本认同;第三个层次的争夺才是最真实的,也就是对信奉资源的争夺。好比说我们日常糊口中有这个信奉需乞降现实的糊口题目,是选择和尚仍是羽士?这个题目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术之争或者效验之争,它不再是我们说的道理之争。
从正史资料和佛教的藏经文献中,佛道之争往往是天子组织的辩论或佛道之间关于信奉历史和基础观念的辩论,羽士好像一直处于下风,这实在是佛道互涉的特殊形态。假如看六朝时的志怪小说,民间日常糊口中的佛道之争往往是信奉资源的竞争。
与此相对,在中国古代文化的大环境中看,佛教进入中国面临的中国人的认同题目则呈现为夷夏之争,这显然不是佛道之争。我们经常提及的佛道之争好像是学理之争,其中还掺杂了政教关系,不妨说,对于佛道之争,我们仍存在一些简化的误区。
可以试想这样一个过程:西域的胡人来到中国,假寓并不断与中国人交流,在这一过程中把自身的信奉观念逐渐描述和传递对方。对于最初的信徒而言,根本题目是信奉认同与民族认同之间的张力。我们是华夏之邦,为什么信奉一个夷狄之神,如何解释信奉一个外来宗教的公道性?这样就不得不面临信奉的公道性及其与本土文化之间的联系关系诠释的题目。
“佛道之争”有无今人描述得那样泾渭分明?
从顾欢的《夷夏论》,及以后的《二道论》《笑道论》等存世文献看,佛道争论十分激烈。事实上,文本之外的信奉实践才是我们需要正视的视角:在日常糊口中,一个羽士也可能信佛,一个佛教徒也可能信道。
好比昙鸾,他从小体弱多病,到陶弘景那里去要随着他学永生不死之术。他的目标是有足够长的生命去钻研精深的佛理。可见,对于他来说并没有非此即彼的差异——或者说,术可以有通用但可以信不同的“道”,即广纳百术而自认一道。
佛道互涉和论辩有三个层面:其一是论理,观念和信奉上的争拗;第二个是文化认同上的争执,也就是夷夏题目;第三个也就是对信奉资源的争夺。夷夏题目不能等同于佛道争论,夷夏题目的本质还是文化认同,顾欢的《夷夏论》并不是仅仅批评佛教的理,而是在批评佛教的糊口方式以及其糊口方式给人们所带来的冲击。他鄙视非中原、非华夏的宗教。
佛道之争中,好像道教是比较被动的,不仅造出一个传说,夸大佛陀是老子变的,而且还大量“抄袭”佛经的内容。如何理解这一题目呢?是否可以从以下两个线索出发:第一是佛教为外来宗教,佛教主张的日常糊口和中国人所主张的传统糊口和传统伦理是有冲突的;第二,需要理解何谓道教的本土性,或者道教对本土性的理解是什么,以及它为什么要说佛教是它的一部门。
柏夷先生的《蚕与菩提树:灵宝派取代佛教的尝试以及我们定位灵宝道教的尝试》中指出《灵宝经》是道教主动想要将佛教融入自身的一种尝试,可谓一针见血、洞见烛照。对道教而言,它并不想消灭佛教,而是想把它改造成自己的一部门;佛教则需要在保持独立性的同时又必需面临文化上的张力。
从这个意义上讲,假如我们仅仅以为佛教和道教是庙堂之上的一种争论,抑或文本和观念之间的鉴戒,这个题目仍旧是一个文化冲突和对信奉本土性的熟悉。
![]()
本文链接:http://djffw.com/post/2179.html
转载声明:本站发布文章及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转载本站文章请注明文章来源!